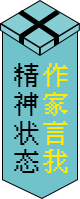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豫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研究:商圣范蠡评传
-
>
图解资本论
-
>
金融炼金术(专业珍藏版)2021专业审订
-
>
博雅丛书系列——经济行为的人文向度
-
>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全球化与国家竞争
-
>
协同创新网络研究
-
>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3231030
- 条形码:9787543231030 ; 978-7-5432-3103-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经济学研究者★ 本土演化经济学原创研究成果集粹 ★ 了解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便捷途径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内容简介
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兴起创生、创新,并由此而导致系统转变的经济学,它不同于新古典的研究范式,是一种非正统经济学,自西方演化经济学自20世纪末被引入到中国以来,我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上已发表了大量论文,但这些论文散布于各种期刊,难见系统。因此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决定从2019年开始,以连续出版物的形式,汇编较有代表性的演化经济学论文,特别关注本土经济学者的原创性成果,本书为其第二期成果。 本书收录了靠前很知名的演化学者的18篇文章。这些文章或是在理论层面探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特征,或是以演化视角来考制度、文化经济周期等要议题,反映了靠前化经济学研究的较高水平,也是不熟悉演化经济学的读者了解这一新兴范式的便捷途径。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目录
编者的话
目录
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 路风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 ——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 贾根良
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受组织的市场:产业政策讨论应有的演化理论基础 / 封凯栋 姜子莹
演化经济周期理论的源头:熊彼特和米切尔的经济周期理论对比 / 张林 陈赤卫
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基于多主体的学习过程 / 黄凯南 乔元波
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及影响 / 马涛
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 / 王焕祥
从众与服从的演化及其“齐美尔”意义 / 杨虎涛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的沟通——以演化经济学为例 / 胡乐明 刘刚
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 刘凤义
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 刘志铭
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沿研究 / 沈尤佳
字典式偏好序与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兼论对制度演化的影响 / 张旭昆
评文化决定论——以江西省余干县中童镇的眼镜业为例 / 李建德
从美元货币创造及其循环机制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和成因——基于马克思—后凯恩斯主权货币理论的分析 / 马国旺 刘思源
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两代人构建理论体系 / 吕守军
制度、企业家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 / 张海丰 杨虎涛
技术选择中是否存在格雷欣法则?——一个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 / 陈明明 张国胜 郑猛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节选
█ 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 路风 目前中国深陷经济下行的周期中,虽然政府屡屡出台刺激政策,但中国经济产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使得此种努力难见成效。2016年第4期《文化纵横》刊登了路风教授的文章《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本文是这篇文章的姊妹篇,二者共同揭示了现行经济政策与产业升级内含的矛盾之处,并指出正是因为现行经济政策的思维框架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引致产业升级的重要性长期遭到忽视。立足于此,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具有扭转下滑趋势、进入新增长阶段的潜力,但前提是经济政策的现行范式发生改变。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可能实现以产业升级为动力的增长。 ▌一、经济政策“新范式”的实践和效果 在21世纪的**个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罕见的高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但由于刺激政策旨在扩大需求,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意识,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加深,致使中国经济积累起许多矛盾。虽然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要求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提供了契机,但是,经济政策却转向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范式”。[1]这一新范式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把市场机制看作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法宝,而把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扫清市场化的障碍,[2]产业升级就是在这个转向中被忽略了。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新范式”的形成经历了这样几步: 1.针对高增长阶段末期产生的矛盾,新的经济政策把问题的根源定义为经济失衡,而失衡则源于政府以投资驱动所导致的粗放增长。为此采取的相应核心政策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导致事实上的紧缩政策)。但这里所谓的“结构性”不是指通常所理解的产业或经济结构,而是阻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结构(如阻碍产品、要素和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那些因素)。新政策的预期是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使经济增长回到健康的轨道。 2.不过,与制定政策的预期相反,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政策变化过程中继续明显下滑。尽管下滑与紧缩政策直接相关,但主导思维却把其原因归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变化,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适中阶段的“新常态”之说。在对“新常态”必然性的论证热潮之中,经济增长在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但是,增长速度再次没有按照预言的那样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是继续一路下滑,引发政府采取“稳增长”的应急措施。 3.完成“新范式”确立的关键一步是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个改革的内容存在不同的解读(如在政治领导人的诠释中显然包含产业升级的内容),我们这里依据经济学家的解读进行概括。根据这种解读,转向“供给侧”的是因为需求管理已经无效,继续实施“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将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因此,增长动力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这就要求政府集中于结构性改革。由于高增长阶段和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中国经济需要先经历一个“市场出清”,然后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后是一个预期: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将使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理想的增长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比较来认识“范式”是如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传统是以“发展”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所以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以GDP的增长或高增长为中心的(因此也造成追逐GDP增长带来的各种弊端)。在这个传统中,改革是为了发展的逻辑始终一贯,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被当作发展的手段——正如“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句名言所说。改革的方法因而也是演进式的,允许尝试。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不执拗于意识形态目标。 “新范式”则在这些根本点上发生了改变:**,发展或经济增长不再是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至少是变成了次要目标;第二,以市场机制将解决一切发展问题为信念,市场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被看作只是发展的手段;第三,政策过程的“实用主义”色彩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替代。如果回忆一下2013~2014年充斥在媒体上的议论,就能感受到那种“宁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停滞,不要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的气氛——这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新范式”的意识形态原则大大压缩了采取实用政策的空间。“新范式”有其理论基础的——不太 容易为社会公众所理解的是在它形成背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即经济政策思维突然转向以一个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框架。这个模型,就是以教科书形式在中国普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本文将其称为“教科书经济学”),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其实质是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理性经济人的效用*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佳社会效率。 由于新古典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处于主流地位,所以它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改革思维,而且还帮助传播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优越性的社会意识。尽管如此,“教科书经济学”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上占据过主导地位。但这一次不同,在塑造经济政策方面,信仰新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阶段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新范式”的形成。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概念——“市场出清”——就是从一般均衡理论直接搬用的。 一般均衡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它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阶段兴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如果个人被允许在没有国家或其他权威干预的条件下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社会将会通过自发的组织机制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深厚的意识形态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古典理论能够逐渐占据“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指的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所有的商品市场能够同时达到供给等于需求(即市场出清),从而使经济体系达到由一系列资源配置和价格所构成的理想状态。对市场经济学家来说,如果能够证明存在着经济体系必然向之运动的一般均衡,那就有了描述经济现象并预言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则性工具,而市场经济的配置效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4]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正如AlanKirman所指出:“这个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能证明,一个经济体从通常经济含义上的非均衡状态能够调整到令人满意的均衡状态。”更糟的是,“即使在我们强加于个人(行为)的严格假设之下,我们也从来不能证明经济系统会稳定于任何不变的状态”。[5]换句简单的话说,一般均衡状态从来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出现过。[6] 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政策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对“新范式”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概括起来说,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经济下滑,从中国现有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的努力也没有奏效,[7]但目前经济政策的主旨却展现出这样一个逻辑:经济下行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体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为了让在高增长阶段特别是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下被“扭曲”的经济恢复平衡,中国经济需要继续经历一个L型(即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其间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淘汰“僵尸企业”等措施达到“市场出清”(其理论含义就是达到一般均衡),再加上“结构性”改革,然后市场机制就可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带来创新和发展。[8] 但也正是与理论结合起来看,这个政策逻辑含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可以表达为两个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回答的问题。 **个问题:如果达到“市场出清”,就必须让中国经济“触底”,但哪里是“底”? 也许是为了化解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悲观情绪,201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在一两年内成功触底”。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而是稳住了,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从文章的逻辑可以看出,“触底”之所以被看作是“转型成功的曙光”,原因就在于它意味着实现了市场出清或一般均衡,此后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将把中国经济带回到增长轨道(虽然不过是“L型的下边”)。但问题在于,所有的类似说法都只不过是猜测。 由于一般均衡状态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过,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事先确定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什么水平就算是“触底”——5%或3%还是1%甚至负增长?从逻辑上讲,是否“触底”只有在经济增长速度被证明已经稳定于某个水平之后或开始反弹之后才可能事后确定。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以“市场出清”为名继续放任增长速度的下滑不会演变成为一场大萧条。恐慌导致经济的螺旋下跌(通货紧缩的机制)是可能的,而“乘数效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明文写着的。面对所有这些在现实经济中曾经甚至反复出现过的可能性,增长速度下滑的唯一底线只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大众和国家政权对于经济恐慌的政治容忍度。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出清”或实现“均衡”之后的市场机制就能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质疑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一般均衡理论把古典经济学传统所关心的价值或财富创造以及经济增长果断地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把分析焦点转向了交换关系、主观的效用价值和资源配置效率。当这个理论把稀缺资源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有效配置当作中心问题后,它也就不会关心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没有去证明经济增长是均衡的结果。与之相反,熊彼特恰恰是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他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循环流转”(circularflow)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9]他后来更是正面地提出:“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10] 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即打破均衡),于是作为发展动力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就不可能仅仅因为资源配置效率就自动发生。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创新的决策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必须来自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虽然也包含发生错误的可能)。对于产生重大产业后果的创新行动,战略性决策的实质并非仅仅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11]因此,产业升级必然要求战略性决策与能力成长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一定是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新范式”抽象掉所有这些问题,遑论回答,其政策陈述中从来没有产业内容,所以也无法证明“市场出清”就会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由于上述两个致命缺陷,所以“新范式”其实是建立在对一个自由市场模型的信仰之上,它的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差不多4年的实践足以证明,“新范式”的经济政策无效。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决策层究竟打算花多大的代价去等待它的*后破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和前景 面对中国经济出现通缩现象,一些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建议实施被“新范式”嗤之以鼻的需求管理或刺激计划。但是,迄今的政策辩论被束缚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和概念中,其主要缺点是没有产业内容。当投资已经被“新范式”妖魔化为纯粹的刺激手段时,这样的讨论并不足以帮助确定政策的方向。因此,本文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把焦点指向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增长速度注定较低的“成熟”阶段?或者反过来问,中国经济是不是本来就能够继续增长,而且有潜力重新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本节即以生产率指标为中心,通过国际比较来证明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增长阶段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潜力。 为从全球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程度,图1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同时为显示发展的动态性质而选择了1960年和2010年两个年份,把各国就业者的人均产出(即劳均GDP)和就业者的人均分摊资本(即劳均资本)两个数据标注出来(以2005年美元计算)。 图1展示的关系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生产函数”,[12]因为图中的劳均GDP可以被看作是劳均资本的函数,其轨迹类似于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图1反映出如下的几组关系(同上)。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更高的劳均资本转化为更多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当劳均资本处于高水平时,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反映出报酬递减规律; 第二,技术进步的效果可以由劳均产出的提高所间接表达出来,但技术进步在实过程中是与资本积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资本积累提高为必要条件的; 第三,穷国的劳均资本提高缓慢或停滞,因此也缺乏技术进步。落在图1左下角的一些国家,其劳均资本在50年间基本未变,它们在2010年的产出也就没有超过1960年的产出,表明没有技术进步; 第四,富国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它们既是在1960年使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国家,也是发明了2010年新技术的国家;由富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向穷国溢出。 图1 (图1.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分布。原始数据来源于PennWorldTable8.1版(它是一个经济学界经常使用的数据库),计价单位是2005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选取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的收入分组标准,选取了47个国家样本。(1)低收入国家选取9个: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塔吉克斯坦,朝鲜,柬埔寨,阿富汗,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2)中等收入国家选取20个:墨西哥,阿根廷,中国,伊朗,智利,俄罗斯,泰国,南非,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土耳其,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乌克兰,巴基斯坦,埃及,巴西;(3)高收入国家选取18个: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爱尔兰,韩国,瑞典,美国,德国,芬兰,意大利,英国,葡萄牙,荷兰,瑞士,比利时。)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更高的劳均资本转化为更多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当劳均资本处于高水平时,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反映出报酬递减规律; 第二,技术进步的效果可以由劳均产出的提高所间接表达出来,但技术进步在实过程中是与资本积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资本积累提高为必要条件的; 第三,穷国的劳均资本提高缓慢或停滞,因此也缺乏技术进步。落在图1左下角的一些国家,其劳均资本在50年间基本未变,它们在2010年的产出也就没有超过1960年的产出,表明没有技术进步; 第四,富国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它们既是在1960年使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国家,也是发明了2010年新技术的国家;由富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向穷国溢出。 图1是从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发展特征的事后概括,其实际内容可以由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出来:英国工业革命首创的工厂制导致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造就了持续的技术进步;[13]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发明出来围绕着电力、化工和内燃机的一系列新技术,而率先通过大规模投资发展出大企业模式的美国和德国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本密集的技术及其后续的创新;[14]二战后出现的核能、航天、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技术及其扩散,继续推高了工业的资本密集度。因此,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互动的两个方面:没有技术进步的投资不会形成有效的产业资本,而技术进步也必然通过投资才得以实现。历史证明,“新范式”要求缩减投资去抓“全要素生产率”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图1以两个正方形标出了中国的位置。左下角的正方形是中国在1960年的位置,右上角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巨大进步,并同样遵循着生产率与资本积累的正相关关系。但同时可见,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10年,中国的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分别不到美国的1/6和1/5,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中国发展水平大致只相当于德国1960年或韩国1980年的水平。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但反过来说,规模优势(如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大工业国)也容易掩盖中国在生产率上与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率特别是工业生产率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库,对中国与其他5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绩效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现有数据的限制,对中国,我们选择1978~2007年(恰好大致相当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数据,而对其他5个国家,均选择1963~1992年的数据(这个选择尤其考虑到与日韩高增长阶段进行比较的需要)。 图2 (图2.中、美、英、德、日、韩6国的工业生产率在30年间的增长倍数。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的衡量单位为2015年美元现价。为了和前面PennWorldTable数据保持相对一致性,本文根据联合国的“按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数据,将各国制造业数据统一换算成按2005年美元计价。) 图2展示了6个国家在30年里,全部门劳均资本、全部门劳均产出和工业劳均产出的总增长率(即期末相对于期初的倍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事实. **,6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率增长无一例外地超过全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在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的全部门劳均中国的全部门劳均GDP增加了4倍,而同期的工业劳均GDP则增加了9倍,说明工业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关系其实具有普遍性。对低收入国家发展过程的研究公认,劳动力从农村流入生产率更高的工厂是一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中长期内会比其他任何经济部门都更强劲。[15] 第二,工业生产率增长*快的国家是从低收入水平一路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日本和韩国:在3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了近35倍,而韩国增长了近32倍,有力证明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水平,然后才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上(即富裕程度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 第三,对低收入国家发展过程的研究公认,劳动力从农村流入生产率更高的工厂是一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中长期内会比其他任何经济部门都更强劲。[15] 中国工业生产率在30年里的增长只超过美国,低于英国和德国,更是大幅度低于日韩,说明以提高生产率为重心的中国工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特别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日韩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会比中国快得多?这是因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迅速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例如,在1960年代初才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韩国,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末就已达到总出口的70%。[16]而中国的工业结构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图3 (图3.中、美、英、德、日、韩6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含量对比。数据来源是基于对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UNCTAD)的分析,并参考德勤咨询《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指数》第6页图2。计算方法参考德勤咨询《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指数》计算方法,把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汽车相关出口产品”的加入到“高技术产品”中。GDP与2011年国际元保持一致。)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刊(2019) 作者简介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是一个非正式学术组织,由国内从事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一批学者(主要是年轻学者)发起,于2008年首次举办,到2018年已举办十届,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和清华大学陈劲教授担任两任主席,年会设秘书处,成员包括复旦大学孟捷、山东大学黄凯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虎涛、云南大学张林等10人。
- >
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
¥18.5¥42.0 - >
李白与唐代文化
李白与唐代文化
¥9.9¥29.8 - >
自卑与超越
自卑与超越
¥13.5¥39.8 - >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37.1¥48.0 - >
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
¥25.9¥39.8 - >
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
¥25.8¥28.0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19.3¥35.0 - >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13.4¥42.0
-
金融炼金术(专业珍藏版)2021专业审订
¥39.6¥55 -
韦伯--经济与社会
¥8.8¥17.9 -
新石油战争:一场重塑世界能源格局的战争
¥15.7¥49 -
国富论
¥14.6¥34 -
国富论彩图馆
¥15.1¥39.8 -
王亚南文选(全三卷)
¥64.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