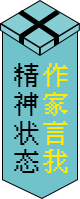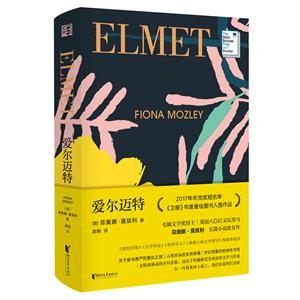-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东京人(全二册)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名人·岁月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伊豆舞女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雪国·琼音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文学自传
-
>
千鹤 碧波千鸟
-
>
古典名著白文本:搜神记
爱尔迈特/(英)菲奥娜.莫兹利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3960551
- 条形码:9787533960551 ; 978-7-5339-6055-1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爱尔迈特/(英)菲奥娜.莫兹利 本书特色
毛姆文学奖得主、《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决选入围作者《卫报》年度*佳图书入围作品,千禧一代的温柔与暴烈之作! 一部让人想起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的惊喜之作一支暗流涌动的乡村悲歌,浸沉于约翰郡荒芜风景的文学与传说关于家与尊严的复仇之旅,人性尽头的生死殊搏布克奖决选作品,英国80后文坛黑马 ☆ 2017年布克奖短名单、《卫报》年度*佳图书入围作品,毛姆文学奖获奖小说。《纽约时报》《文学评论》《经济学人》《出版人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金融时报》等一致推荐。 ☆ 千禧一代极具潜力的文坛新锐、80后英国女作家长篇小说处女作。作者生于1988年,即凭此书入围201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决选名单,以及女性小说奖、狄兰·托马斯国际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 ☆ 聚焦家庭、阶级、暴力,以及性别认同、乡土归属等众多现实议题,以小说编织出一幅浸沉于约克郡历史与文学传说的“虚构挂毯”。以一家三口搬家归隐的故事展开,试图讲述一个揭露人性善恶的乡土寓言,呈现作者宽阔的写作视野。《纽约时报》评价此作“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下,如同可以发生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的故事。” ☆ 小说语言糅合了诗意与暴烈、精细与冗长的书写风格;译文流畅、简洁,忠于原著。让人想起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休斯的动人诗行,或是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语言中的蛮荒风景”。小说带领着读者,在温柔与暴烈的缝隙之中展开对人性的勘探。 ☆ “宁静的爆炸之作——精致且令人难忘。”——《经济学人》☆ “一支乡村悲歌——(《爱尔迈特》)一颗伤痕累累的黑色宝石。”——《卫报》☆ “一部充满诗意、神话般的作品,菲奥娜·莫兹利对讲故事的绝对自信,带领着读者启航。”——《纽约时报》☆ “一部坚实而强有力的作品,混杂了诗意与暴力,让人不禁想起科马克·麦卡锡。”——《出版人周刊》☆ “节奏感与顿挫感十足,梦幻般的诗性书写,《爱尔迈特》是一个丰富的尘世寓言。”——《金融时报》☆ “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说,书写家庭关系、家园、农村开发、暴力,以及*重要的是,对受困中孩子的矢志不渝的忠诚和爱。”——《伦敦晚报》☆ “一部跨越世纪的小说。既是当下,也是对过往历史的回顾。”——《文学评论》☆ “一个语言明净、结构精巧的哥特式乡土寓言——《爱尔迈特》是一部非凡之作。”——《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爱尔迈特/(英)菲奥娜.莫兹利 内容简介
《爱尔迈特》是一部描写家庭关系、土地与家园归属的长篇小说。小说入围2017年布克奖短名单、《卫报》年度很好图书,作者凭借此书斩获毛姆文学奖,入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等众多文学奖项决选名单。 小说的故事发生地英国约克郡,是古时爱尔迈特王国的所在地。约翰一家从小镇搬到此地,在一处树林里展开新生活。父亲约翰体型高大,像个巨人,靠打猎和做体力活来维持一家生计,以地下格斗挣取额外收入。凯茜和丹尼尔姐弟俩,平日则在树林里玩耍、自造弓箭,定时去邻居家学习。日子虽艰辛,却也算安稳平静。 直到地主普莱斯先生的出现,约翰一家生活和命运的节奏从此被打破。普莱斯对租户层层压迫与剥削,使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与此同时,父亲和凯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家,以及同是租户的邻居们。但无法调和的矛盾,很终还是将他们带往了暴力与死亡的结局。原本安宁的家被打散,从此被打散,丹尼尔踏上找寻亲人的旅程…… 小说由主人公——十四岁男孩丹尼尔讲述,语言清澈、细腻,充满诗意。小说直面英国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家庭,阶级与土地的隔阂与分裂等种种现实议题,很后又以丹尼尔矢志不渝的爱与忠诚寻求希望与出路。
爱尔迈特/(英)菲奥娜.莫兹利 节选
**章 我们是夏天来的,当时四野繁花盛开,白天又长又热,天光柔和。我走到哪儿都不穿衬衫,任由汗水干净地流淌,享受着浓稠空气的抱拥。那几个月里,我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晒出了雀斑。太阳落得好慢,夜在黑幕合下与天光重现之前都是青灰色的。兔子在田野中嬉游,遇到运气够好,没有风,山间罩下一层薄纱,我们还能见到一只野兔。 农夫们开枪打兔子,我们挖陷阱抓兔子,为的是吃肉。但抓不到那只野兔。我的那只野兔。那是只雌兔,她和她那一家子把窝筑在铁轨遮挡的地方。对于火车来来往往她已经无动于衷。我看见她溜出窝来的时候,都只见到她一个,那样子大摇大摆,仿佛觉得自己根本不会被人看见,也不会被人听到。对于兔子来说,在夏天,撇下家里的小家伙们,到田野中跑来跑去,是很难得一见的。要么是在觅食,要么是在求偶。她寻寻觅觅的姿态,仿佛自己平日里是个捕食者;仿佛她作为一只兔子思虑再三,决定不再当别的动物的猎物,要改为跑来跑去捕食别的动物了;仿佛她作为一只兔子,某天发现自己在被一只狐狸追赶,然后突然停了下来,掉头反追起狐狸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她跟别的兔子不一样。她猛然蹿出的时候,我简直看不清她的身形;可当她骤然停下的时候,又成了方圆几里内蕞蕞安静的东西。比橡树和松树还要安静。甚至比岩石和电缆塔还要安静。比铁路轨道还要安静。就好像她抓住了大地,将它紧紧按住,成为了大地的中心,即便是周遭延伸至极远处范围内蕞平静、蕞无害的地表上的物体,所有的一切,都被她那大到夸张的、球形的琥珀色眼睛尽收在内。 如果说这只野兔充满了神奇,那她脚下抓挠着的这片土地也同样如此。如今,这里只如人脸上的麻子一般缀着一小丛一小丛的树,而曾几何时,整个郡都还是蓊蓊郁郁的森林,风起之时,林间荡起一片絮语,叫人想起古老森林的魂魄。这里的土壤中埋藏着许多失传的故事,它们曾在这里流传,在这里衰朽,又在这里再次凝聚成形,自灌木丛中升腾而起,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矮树丛后面会有传说中的绿人朝外窥探,他们的脸是树叶,而腿脚是扭曲盘错的树枝。饥肠辘辘的猎犬在这里喘着粗气飞扑向拼命逃逸的猎物,口中发出狺狺的狂吠。罗宾汉和他那群瘦骨嶙峋的流浪汉在此吹着口哨,摔跤做耍,大吃大喝,跟鸟儿一样自由,而鸟儿们的美丽羽毛恰也是他们从贵族们那里盗来的战利品之一。古老的森林自北向南,绵延而下。这里栖息着野猪、熊、狼和鹿,地面上覆盖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各种菌类,还有雪花莲、圆叶风铃草和报春花。然而很久以前,森林便让位给了庄稼、牧场、道路、房屋和铁路轨道,只留下了我们这儿这样的一蓬蓬的小树林。 爸爸、凯茜和我住在一栋小房子里,房子是爸爸用四周土地上找到的材料自己盖的。他替我们选的地方是离东海岸铁路干线隔了两片田地的一座白蜡树小树林。既够远,可以不被铁路上往来的人看到;又够近,可以把火车的往来情形弄得清清楚楚。我们时不时地就能听见火车的声响:客车传来的是嘈杂的人声和铃声,货车那画着纹章的铁皮车厢满载货物经过时,则是哽咽和大喘气。它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和间隔,每趟旅程,都围绕着我们的房子画下一道道年轮,又宛如荡过一阵阵祈祷的钟声。“阿德兰蒂斯”号和“潘多利诺斯”号列车像长长的靛蓝色带子从伦敦驶向爱丁堡。小一些的火车的服役时间更长些,电弓上带着斑斑的锈迹,开起来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老旧的车尾列车跑起来吭哧吭哧的,疲态尽显。对于比它们年轻的铁轨来说,它们跑得太慢了;在热辊压榨的铁轨上滑行的那副样子,活脱脱像是冰面上的老人。 在我们刚到的那天,一个有点年纪的二等兵开着一辆铰接式货车上了山,车上满载着有裂缝的、别人不要的石材,那是从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拉来的。卸货基本上都是爸爸一个人的事,那个二等兵就只坐在一根刚伐下的原木上,一根接一根地抽凯茜自己用烟草和纸卷出来的香烟。凯茜用手指搓烟卷,然后从齿间伸出舌头来舔一下,把烟卷封上,他就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把装烟草的小袋子放在右边的腿上,他就盯着她的腿,还不止一次地凑过去拿起小袋子,有意无意地拂到她的手,然后假模假式地看看袋子上的字儿。每次他都主动要替她点烟,热切地举着火等她,凯茜每次都不领情,自己给自己点上,弄得他像个小孩子似的,还颇有些气恼。他没看到的是,在给他卷烟的时候,她一直都皱着眉头,怒冲冲地瞪着自己的双手。他不是一个有眼色的人,人家明明都摆在脸上了,他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无法从别人的眼神和嘴角读出别人心里想说的话,也无法想象,漂亮的脸蛋下面所包藏的,未必就是漂亮的心思。 整个下午,二等兵的嘴一直没停过,讲部队里的事儿,讲他在伊拉克和波斯尼亚经历过的战斗,讲他亲眼见过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被人用刀子开膛破肚,讲他们的内脏会短暂地呈现出蓝色。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他的语气中几乎没有丝毫的阴郁。爸爸整天都在房子上忙活,到了晚上,两个大人走下山坡,去喝二等兵带来的装在塑料瓶里的苹果酒。爸爸并没有待多久。他不喜欢多喝,而且除了姐姐和我,他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 回来以后,爸爸告诉我们,他跟那个二等兵吵了一架。他用左拳朝他脑袋上来了一下,所以拇指指节那儿多了一道血痕。 我问他是怎么吵起来的。 “他是个混蛋,丹尼尔。”爸爸说,“他就是个混蛋。” 凯茜和我觉得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我们的房子,设计得就像任何一个小城市里城乡结合部的那种平房或活动住房,老人和穷人住的那种。爸爸不是个建筑师,但他能从镇公所搞到一份灰白色的示意图,并照着图把房子给盖起来。 不过我们的房子要比其他同类的房子结实得多。盖房子用的砖、砂浆、石材和木料都比它们要好。我知道,跟我们进城路上看到的那些房子相比,我们的房子肯定能多撑好多年。还比它们要漂亮。从树林里蔓延出来的青苔与藤蔓,更急切地想要攀上它四面的墙,更愿意将它拖入到原先的风景中,跟自己融为一体。每过一个季节,房子便显得比原先更老旧一些,而它看上去存在于那里的时日越久,我们便知道它将愈加持久地存在下去。就像所有那些真正的房子,就像所有那些人们称为的家。 外墙刚一树起来,我就播下了各式种子,插下了各种块茎。土地经过爸爸蕞初的开垦后依然敞开着怀抱。我把家中的几个食槽加长拓宽,往里面装满了蔬菜制成的堆肥和我们从一个马厩里问人要来的新鲜粪肥。那个马厩在离我们这儿八英里远的地方,那儿有个灯光马场,会有小姑娘们穿着浅棕色的小马裤和亮闪闪的皮马靴在马场里绕圈子。我种下了各种颜色的三色堇、水仙、玫瑰和一根从一株开白花的攀援植物上剪下来的插条,那株植物从一堵老旧斑驳的清水石墙里逾墙而出,正巧就被我发现了。 这时节并不适合栽种,但有些嫩芽还是冒了出来,更多的在第二年露了头。等待才是一栋真正的房子题中应有之义。等待使房子成为我们的房子,等待使它根深蒂固,等待将房子和我们嵌入季节,嵌入岁月。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十四岁生日将近,而凯茜则刚满十五岁。时间是初夏,这给了父亲盖房子的时间。他知道我们绝对可以在冬天不到就全部完工,而到九月中的时候,房子就已经会有个大概的样子,能住进去了。在那之前,我们暂时把家安在两辆从部队里退役下来的厢式车上,那是爸爸在唐卡斯特从一个小偷手里买来后,沿着土路和小径一直开到这里来的。我们用钢索把它们连到一块儿,再用防水帆布在上面一张开,显得很专业的样子,待在下面便很有安全感了。爸爸睡在一辆车里,凯茜和我睡在另一辆里。帆布篷下面还摆了几把饱经风吹雨淋的塑料花园椅,过了一阵后,又添了一把塌陷了的蓝色沙发。这里便成了我们的客厅。温暖的夏夜里,若是无事可做,我们便把大纸箱倒过来,放上马克杯和盘子,也把脚搁上去,就那样懒坐、闲聊、吟唱。 在天气蕞为清朗的夜里,我们会在外面一直待到天亮。我们把两辆车上的收音机同时打开,凯茜和我便在铺满落叶的地上,伴着我们的林间立体声音响翩翩起舞。随便哪个邻居都与我们隔着好远,所以我们很放心,不怕有人听到。有时候我们不开收音机,就坐在那里自己唱。几年前,爸爸给我买过一管木笛,给凯茜买过一把小提琴。在还有学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学校里上过免费的课程。虽然我们算不上专家,但演奏出来的效果倒颇为悦耳,因为这两样乐器本身的音色就相当棒。爸爸很会挑东西。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东西是好是坏他可会挑了。从木料、胶水、清漆的味道和边缘的光滑程度,他就能判断出做工和质量。这两件乐器可是他开了半天车跑到利兹去买来的呢。 所以你看,他对不同林木间的差别是很在行的。我们如今住的这片林子中的树,他早就认识,还专门跟我一一讲过。这里所有的树,几乎都介于树苗和五十年树龄之间,因为在我们搬到这里来之前很久,这片树林就有人修剪过。爸爸觉得修剪了甚至有几百年。在树林正中心的地方,长着一批树龄更久的树,其中一棵是它们之中蕞年长的。那是它们的母亲,爸爸说,所有别的树都是从她那儿来的。她在那儿长了超过两百年,树皮都已经硬结了,像刮过的贝壳杉胶。 林子里还有榛树,有些还会掉下榛果来。爸爸用一把折叠刀从树干上割下树枝,然后教给我看怎样加工嫩枝。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想要用新鲜的嫩枝做一根细细的笛子。我先削掉软软的树皮,再用半圆凿掏空树枝芯子里的肉。我干得很仔细,尽力把外表弄得十分光滑,像手指一样呈现出弧度。可这根笛子怎么也吹不响。自那以后,我就渐渐开始转向做有用的东西,不那么需要技巧的东西,或者说即便样子马虎一点也一样能管用的东西。只要碗能装东西,哪怕样子丑一点,做工粗糙一点,人们也还是会管它叫碗。但笛子要是吹不出乐音来,就不能叫笛子。 我们树林中的家有一个厨房,还有一张橡木大桌子。我们还在厢式车里露营的时候,爸爸就是用烧烤架为我们做饭的。这套架子是他用几片波纹铁皮自己做的,烧烤用的炭则是他用两只油桶在林子正中那棵老母树旁边自己烧的。 那段时间我们吃了太多的肉。在和他一起找到定居之所前,我们只能是他给自己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而他吃的主要是自己的打猎所得。他根本不讲究要吃水果或蔬菜。他常打的东西是斑鸠、原鸽、领鸽、野鸡和鸟鹬,如果他能在夜里逮到它们从藏身之所出来的话。这里附近还有毛冠鹿出没。如果没什么东西好打,或是口袋里有了现钱,或者纯粹就是想换换口味了,他会跑到村里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些牛肉、羊肉或是肉肠回来。若季节合适,还会有一些能在早餐吃的小猎物。村子里有个人养了只灰背隼,替他抓来了好些云雀,他一个人吃不了,就拿来跟我们换那些灰背隼抓不了的大鸟。我们吃云雀烤面包,几乎连面包带云雀全都吃下去,就着一杯杯热乎乎的奶茶。 有一次,爸爸跟一些流浪汉一起出去了四天,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麻袋拔了毛的鸭子和五板条箱的活鸡。他在我们房子待建的后门附近建了一个鸡舍,把那些鸡养了起来。自那以后我们就有鸡蛋吃了,可还是很少吃蔬菜或水果,除了从路边摘的各种浆果。 后来,直到房子盖好后,我才种了苹果树和李树;爸爸有事去村里的时候,带回了一袋袋的胡萝卜和欧防风。我在擦洗干净的厨房案桌上收拾他带回家来的东西,用的是爸爸磨过的大小刀具。 在房子盖好前那短短几个月里,也就是我们露营和唱歌的那段又热又干的时间里,爸爸跟我们好好聊过。他话不多,不过我们听到了很多东西。他谈到了跟谁打过仗,又杀过哪些人,在爱尔兰的泥炭田或是林肯郡的黑土地,那里的泥土都会像法医墨水一样一直沾在双手和双脚上。爸爸曾经打过不戴拳套的拳击比赛,绝不是在体育馆或大礼堂那种地方打,但这种比赛赌注大奖金高,来自全国各地带着来路不明的现金的人会来押他赢。谁要是不赌我爸爸赢那准是傻瓜。他只需一记重拳就能把一个大男人击倒,而要是一时半会儿没击倒的话,也只是因为他想要打得稍微尽兴点而已。 拳击比赛是由那些流浪汉或是周围的一些粗汉们安排的,他们想要有机会试试自己的身手,赚上一笔小钱。流浪汉用这种方式打斗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管这个叫“赏金格斗”或“公平格斗”。他们既不戴有衬垫的拳击手套,也不把比赛分成回合,当中夹着休息。他们格斗时不会有代表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而是非要打到有人投降或是躺倒在地慢慢变冷。有时候,这样的格斗被用来平息两个敌对帮派之间的争端,但多半还是为钱。会有成千上万镑的钱付出去,爸爸能靠打拳过上不错的生活。 爸爸告诉我们,在乔伊斯和奎因麦克多纳两个流浪家族之间存在着延续了几十年的不和。每隔三年左右,两家便会各自派出代表自家的年轻人进行一对一的无拳套拳击赛,由中立家族的长者来当裁判。在这样的场合中,这些家族自己是不能在场的,怕两大帮派间发生混战,因此这两家的男女老少和流浪汉中所有的帮派群体要么被清出了场外,要么被警方逮捕,塞进厢式车里,送进监狱。 这种比赛是很有赚头的。这些为家族世仇而举行的格斗赛往往有很高的彩头。乔伊斯家族和奎因麦克多纳家族彼此会暗中较量,看谁愿意码出的赏金多。有时候两边的赏金会各自高达五万镑,而获胜的人可以把赏金全部拿回自己的大篷车队,请自己的全部伙伴们来个彻夜的威士忌狂欢。爸爸说这帮流浪汉需要格斗赛。他说,经过这么些年以后,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已经无所谓了,但每次只要哪家的某个大人物缺钱了,很有可能就会想个名目出来打上一场,希望能赚上一票。此事早就已经超过了尊严之争,是事关大笔的赏金了。 对爸爸来说当然也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流浪汉,所以世仇不世仇对我们毫无意义。他去打的那些比赛都是有钱的,在那些比赛中,流浪汉或吉普赛人、粗野的农民、城里来的罪犯、地下夜店和酒吧的老板、毒贩子和暴徒,或仅仅是靠拳头吃饭的人济济一堂,他们都带着钱来,想要赢得更多。爸爸到那儿的时候,穿了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扣子全都扣着的短夹克。一个专门操办这类事的人在电话上告知他时间地点,委托他操办的不是那些流浪汉就是别的什么人。爸爸平静地等待着,身边围着的都是他的崇拜者。他是个能只说一句绝不说两句的人,也很少跟别人目光对视。周围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商定赔率,爸爸掉头看向别处,独自平静地踱着步。
爱尔迈特/(英)菲奥娜.莫兹利 作者简介
菲奥娜??莫兹利(Fiona Mozley) 英国新锐小说家,约克大学中世纪史方向博士。生于1988年,成长于英国约克郡。 《爱尔迈特》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入围2017年布克奖短名单、《卫报》年度蕞佳图书、2018年女性小说奖长名单、狄兰??托马斯国际文学奖。作者也凭借此书斩获2018年毛姆文学奖,入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等众多文学奖项决选名单。 【译者简介】 吴刚 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从事文学翻译二十八年,有四百多万字文学翻译作品。翻译代表作有《霍比特人》《我们的村庄》《野性的呼唤》《白牙》《催眠之眼》《战时灯火》等。2016年获得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翻译新人奖”。
- >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13.0¥26.0 - >
诗经-先民的歌唱
诗经-先民的歌唱
¥15.9¥39.8 - >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40.6¥58.0 - >
月亮虎
月亮虎
¥15.4¥48.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5.4¥68.0 - >
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自编集
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自编集
¥6.9¥16.0 - >
烟与镜
烟与镜
¥18.2¥48.0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有舍有得是人生
¥21.2¥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