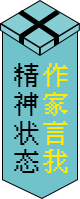-
>
我与父辈(九品)
-
>
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彩虹几度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古都·虹
-
>
(精)川端康成经典辑丛:舞姬·再婚者
-
>
碧轩吟稿
-
>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第三辑)(全十五册)
九月寓言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8088778
- 条形码:9787508088778 ; 978-7-5080-8877-8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九月寓言 本书特色
《九月寓言》虚构了一个从遥远的异地迁徙来的小村故事。这个小村的人们多少年来一直保留着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和行为等征,因而被当地人永久地嘲弄。然而,小村的生活却是那么宁静而热烈,村民们悲苦喜乐的情感命运交织出一幅自足的农业文明景观。不过,在现代工业文化的侵蚀下,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村,终于悲壮地沉落了……
九月寓言 内容简介
华夏版“典藏文库”,旨在——精选当代中国*影响力的作家*影响力的杰作,组成坚实的阵容,陆续推出,形成系列。 目前已经出版 《羊的门》(李佩甫)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张一弓) 《九月寓言》(张炜)。 贾平凹的两部作品正在商谈中,有望今年十一月推出。
九月寓言 目录
九月寓言 相关资料
张炜的精神哲学 李洁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能在历史上立足的作家,是有能力提出和坚持一种精神哲学的人,古今中外,庶几如此。 20世纪后50年,中国文学萎靡不振,跟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颇有关联。 在这“屈指可数”的作家行列中,我认为张炜拥有一个属于他的位置。 张炜是勤奋的写作者。在2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作品群。对研究者而言,这些作品,复杂而多样,存在各种解读的可能性,无论艺术上或思想上都是如此;例如,仅就长篇而言,《九月寓言》之后,张炜的创作便发生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而探讨一位具有张炜那种性质的作家的精神世界,通常采取的途径不外两条,一是研究他的变化和这些变化的原因,再有,则相反——研究他诸多改变当中保持不变的东西;这二者,无疑都有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 本文选择的是第二条途径。这首先因为,读书界和评论界对《九月寓言》以后——或笼统来说90年代以后——张炜的变化,普通较为瞩目,议论也颇多繁,几乎成为人所共见的现象,如此,则何烦我由这篇文章再作饶舌;反之,在这种关于张炜90年代之变的议论里,我尚未看见有人试图为我们指出张炜所坚持和未弃的是什么。这种失察,同那种关于张炜如何与市场经济“新时代”为敌的论调相互辉映,造成了人们下面一个误解:好像张炜是因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而不是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诚然,在80年代,张炜跟外部世界的价值对抗,从不曾表现出像90年代这样的激烈程度;尽管他的《古船》蕴涵了类似的冲突,并且招致了不公正的对待(人们大多认为,《古船》无缘茅盾文学奖是不近情理的),但在事实上,我们没有看见这种冲突影响了他的创作状态,准确地说,没有看到他让自己的创作被这种冲突所影响,在80年代,作为作家的他,是自足的、平静的,与外界保持着适当距离甚至略微有些隔绝。然而90年代,他与外界直接对抗的机会,突然增多了,1993-1996年间,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成为文学以至整个人文界的一个焦点人物(所谓“二张一韩”,即指张炜、张承志、韩少功)。对每个熟知张炜文学生涯的人来说,这种局面相当意外:此人此前默默写作了近20年,除了不断发表和出版有份量的作品供人阅读外,似乎很少做别的事情。在这一方面,张承志、韩少功多少还有所不同,他们自80年代中期起,始终就是“弄潮儿”型作家,在全国范围内异常活跃;而张炜,尽管创作实力超卓,行迹却通常限于本省,以至于习惯藏在不为人知的什么小屋内读书和写作,当时文学正在炙手可热之际,但各种热门场合并不怎么看到他的身影。不料,在完成《九月寓言》后,这个深藏不露的作家,突然频出江湖,挑起“事端”,以最直接的方式立言,伸张其主张;不惟如是,连同他的创作也随之风格一变,《古船》、《九月寓言》中《史记》般的沉着和宽广,让与了《柏慧》、《家族》中《奥德赛》般的忧愤和崇高,叙事风范从堂正本色的良史一变而为心潮难平的诗人……无疑,变化是明显的,就连张炜本人也提到他在八九十年代经历着不同的心态:“八十年代,那时的精神环境刻板一些,也规矩一些;一规矩,人的心情就不太苦。现在不那么规矩了,让人心苦,可是也能从苦中品出甘味。人和艺术要走向深远,就非要经受这苦不可”。 然而,在承认和面对张炜这种明显的变化的同时,有谁留心过他的现在与过去的思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有谁注意到他所有在90年代引起争议并将他变成一个所谓焦点人物的主要观点,其实都是在80年代便已道出的?就此,允许我开列下面一份文章清单,它们都作于1987-1988年间: 《文学是忧虑的,不通俗的》 《关怀巨大的事物》 《缺少稳定的情感》 《缺少说教》 《缺少不宽容》 《缺少保守主义》 这些文章,仅从其标题里已可明其义,90年代张炜言论中为人称誉或诟病的那些内容,诸如“人文关怀”、“道德理想主义”、“不宽容”、“抵抗投降”、“坚持操守”……皆在其中,至于其他更大量的文章,倘费心翻翻《张炜文集》各卷,则极易找到更多说明那些被当作其90年代之变的思想,全形成于80年代且一以贯之的证据。 本文立论的前提即在于此。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的作家,如果不是这样,反倒有乖理数了。我们自历史上得一常识:成熟的、具大气象的作家,其一生治文,尽管多有变化、绝不单调,以致不同的艺术时期还会存在较大的反差,如20年代与30年代的鲁迅、青年托尔斯泰与老年托尔斯泰。但是,这种变化肯定不是朝秦暮楚,不是川戏式“变脸”,甚至应说,在一切已达成大作家素质的人身上,变是相对的,不变是绝对的;不变的,是其精神之根,是其人格、信仰、美学观的基本原则,所变者,不过是这些原则与当下现实境况相整合相激发的反应方式。其实,这又何止是作家素质之差?一切人,不论所操何业,高卑大小亦悉由此分。四百年前,张岱因其弟毅儒编《明诗存》前后之变,致信痛诋曰:“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这“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一语,精辟之至,堪当我们界分大人和小人、大匠和小工、大心和小慧的一柄标尺。 以今下时势,我颇知能赞同以下观点的人微乎其微,但我仍不惮于并且坚持着将其写在这里:对于“作家”——我特意说明此词对象是指,运用语言艺术创造一部分人类文明的人们——来说,份量的大小,绝不取决于单个作品的优劣,而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和表现出其具有自足、稳固的精神哲学。这观点的陈旧,是一望可知的。自从结构主义消解了“主体”价值以及后现代主义粉碎了“知识分子”概念以来,有关文学艺术与高尚精神之间的联系,早已成为嘻笑者的谈资,更何况近半百之年以来中国文人还经历了种种精神的喜剧?然而我所以仍冒同道耻笑之辱,来谈论这么不合时宜的观点,却只是由于对历史尚存一点畏惧之心;我无非让自己的判断质诸理性,然后听到了这样的话语:历史乃“大道”,这个那个“主义”不足为凭,可怜的喜剧记忆也不能永存;倘若自古以来文学的历史有规可循、始终是照某种逻辑写就,我们就不必被耳旁一些嘈扰之声所困惑。于是,我坚定接受了如下的事实:宋玉之愧屈子,非其文采输逊;陶潜之睨同侪,实因境界超拔;杜甫之谓诗圣,岂独诗内了得?《红楼》之成绝唱,终在襟天抱地! 我一再从张炜文中读到“大心”一词,这是一个很有他思想特色的词,是一个融合了他理想的词。上面提到的几位古代中国文学巨人,应在此词所指之中。诚然,现在的张炜远不能与这些“大心”同伍。但我想说的是,文人作家亦和日常社会一样,是以群分、以类聚的;有的人尽管眼下尚未长出“大心”,但他有这样的素质,可以做这指望、为之努力,而有的人,则干脆想也不必这样去想。这绝非主张人的天性有尊卑之分,对此我其实相信孟子的人人皆可致尧舜的看法——当然,我同样相信人人皆可成盗跖;重要的在于,人们鼓励或纵容自己接近怎样的心灵,近墨则黑,近朱则赤,一切皆差在一念,而一念则无非系于人性之善恶的两端。这是何其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千百次的简单聚集起来,却意味着艰难。 论及此,如果说人类文学史(无论中外)是有“传统”的,如果说人类文学史在这“传统”以外也是有“另类”的,那么,张炜无疑走在“传统”的里面而绝非“另类”。“传统”一词,近世以来在许多场合变成一个贬义词,或许不无道理;但据我看,文学中的“传统”——亦即人类文学赖以生长延续下来的那种力量——却与别处不同,它一直是正面的、高贵的,也是不朽的。二三年来,在我们这里“另类”突然成为一个时髦的好词,一些写作者争以“另类”自况,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动机;倘使他们是作为社会现实对立面意义上的“另类”,我欣赏他们的勇气,但倘使他们竟欲充当文学传统的“另类”且以此为荣,则我唯能报以惊骇了!当然,文学史在其高尚的传统之外,历来也不乏各种各样敢然地背叛这种传统的“另类”,如那些泯灭良知专做拍马谀奉文章的,如那些无病呻吟将文学降低为文字游戏的,如那些变卖灵魂假文学实现某种野心的,如那些狐假虎威而压制文学活泼真实的生命的,如一切为着个人名利而轻慢文学、羞辱文学,将文学无聊化、庸俗化、卑微化的……这种种行径,即我所理解的文学之“另类”,而文学的“道统”,则是从屈原到鲁迅,从荷马到托尔斯泰所一脉相承的那种高洁的心史——这也是文学最值得自豪处,它跟世上许多其他东西比,大约是平凡以至寒酸的,但是,它拥有一种好的伟大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面前,人类的某些别的事物却不得不掩面遮羞。 我想,正是被这一传统的光荣所感染,张炜才那样欣然地自命“保守主义者”。细思量,我们确实有何理由害怕成为文学的“保守主义者”呢,既然所保所守的是上述那样一种荣耀以及一颗颗扑扑跳动的“大心”,而非什么下作委琐之物? 不过,就此应加澄清的一点是,人类文学中成为“传统”的那一种力量,它的强大倒并不体现为“人多势众”,而体现为时间的永恒性,体现为从过去向未来延伸和渗透的不死不灭的必然性。倘就广泛性而言,构成人类文学“传统”的作家作品,其实是文学史中的少数派,相反,“另类”倒通常是多数派;不信,请看屈杜一流人物古代文学能得几许?鲁迅一流人物现代文学能得几许?而与这“传统”相反或无关的,却可谓“浩若烟海”。至于原因,则实在简单:文学是关乎精神关乎信仰的,而大多数作家和被生老病死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一般人一样,并不真正有自己的信仰,而是信人之信、欲人之欲,被社会和时势所同化和裹挟着。远不论,仅80年代至今,一代代作家乘势而起顺势而亡的现象,已足显我们文学不知其守、唯能投机的病状。要想找到几位抱定初衷(且有初衷可抱)、十数年而持己见不弃精神的作家,难、难、难! 正因“难”,才显出张炜的可贵。在这个变色龙般的文坛,他是仅有的几个在艺术哲学和精神哲学上保持了连贯性的作家之一,并且是在格物致知、反心为诚的真正个人化的意义上。后半句,又让我生出与“另类”一词相似的感想;如今“个人化”的使用,也是滥之又滥,竟然连许多分明时尚化的小说,也享受“个人化”的誉美——难道汉语真的已经成了一套废物语言,连最简单的意思也表达不清而如此易招误解吗?倘非这样,则“个人化”明明是“集体化”的反义词,那些投合流行文化口味的作品如何称得“个人化”?个人化,一定会在潮流之外,一定是不惧物议、孑然独行。因此在我看来,对一个在90年代仍以“人民性”观点论文学的作家使用这个词,才是恰当的。 一次,与某校大学生对话的时候,张炜被问及:“您真的认为作家应该为人民写作吗?”口气中透出不信或好奇;而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我真的认为。我想那些真正志存高远的作家都在为人民写作。”接着他加重语气说:“要理解人民这个概念。”“人民性”一词,在当代文论术语里面可谓老态龙钟。它出现于50年代,是作为尝试沟通文学的高尚传统与当下文学的进步性的关系词出现的,可是这种用心很快因被认为抹煞“阶级性”而遭到打击,成为批判对象之一。70年代末,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文学概念课堂上曾恢复使用过它,但未过多久,就被“人性”取代了;又未过多久,连“人性”也不谈或者耻于谈了。这样命乖运蹇、孤寂寥落的一个文学理念,张炜却不弃,视为写作的立命之本;假使不是出于格物致知、反心为诚的深慎之思,是无从解释的。读张炜言论,几乎看不到一个时髦、流行、新潮的字眼;一方面这说明他的朴实,另一方面,恰也表示了他对通俗化的拒绝态度,以及一切言谈发乎本心、勿由外铄我的个人化立场。昔孔子言:“辞达而已矣。”意谓:言语,但能达于本心就够了。这讲的,其实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语言的变化,常由思想表达受阻引起;然而,又非一切嗜变的语言表达都有新思维作为背景;这两者间,毋宁说后一种情形在现实中更多见。对当代文坛,我们多有“失语”的感受,这感受并不是指人们陷在无言以对的状况,相反,恰指陷在一种多语而辞不达意以至于连自己亦不知所云的境地——这当然源于内心价值标尺的迷乱。但张炜却有幸避免陷在其中,他的表达,简单、明确、透彻,知道自己内心的原则,所以不迷乱。 例如“人民”这个概念。张炜轻易不用“人”的概念,而反复地执着地使用着“人民”。其原因,在研究他的小说和言论后,也是非常清晰的。这两个词在张炜那里的差异,乃是基于一种道德批判。总的来说,同中国古代先贤所持的实践哲学观点一样,对“人”这个字眼张炜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他不喜欢泛人论,不认为一切与“人”的字眼相关的事物便是好的和善的;他随时警惕着抽象人性论的误区,警惕着社会化的形形色色的人,并把这种眼光施诸创作,来构成他对人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读张炜所有作品,不论写于80年代的或90年代的,也不论是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还是在散文随笔的自白直陈中,你会发现“劳动”和“劳动者”这两个词占有特殊的地位,不光出现密度大,而且一经出现往往便与作家本人的最高道德理想、美学理想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正是张炜精神哲学的一条界限,它的一边,站立着善、美,另一边,站立着恶、丑;进而言之,如果说这个人心目中有什么“宗教”的话,那么,对“劳动”的信仰和对“劳动者”尊崇,便是他的宗教!他所以鲜谈抽象的“人”而喜谈“人民”,原因亦正在此——所谓“人民”,在他那里,就是在世上辛勤、认真劳作的人们,就是“劳动者”! 论至此,我们对张炜的内心秘密便了如指掌,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从80年代初到世纪末,他的创作包括五六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以及六十万字左右的散文随笔,涉及的对象包括乡村、城市、历史和知识分子,文体跨越散文、诗、小说、语录,而风格变化也是起伏不定、简繁交织,但是,所以这一切,都源于或者说支撑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劳动神圣”。为他最早赢得全国声誉的《秋天的思索》(1983),表现的是劳动者的愤怒,“他(王三江)不知捣了多少鬼,坑害了咱们这些没白没黑种葡萄的人!”《护秋之夜》(1984)讲述游手好闲之辈对劳动果实的觊觎,及其可悲的下场。《海边的雪》(1984)可以视为一座铜雕,金豹、老刚这两个与大海搏斗了一生的老渔夫,周身凝聚着来自自然的力量与美。《黑鲨洋》(1984)的主人公,是一群海明威式的不屈的硬汉。《冬景》(1987)不免有些凄凉,因为那个用苦劳创造自己一生并影响和培养了三个同样朴素的劳动者儿子的老人,如今孤苦余生,身边只剩下最小的渐染好逸之风的小儿子。而长篇杰作《古船》虽然主题多层,但我认为其本质的一点在于,它属于劳动者;书中情节充满了历史的恩怨与纠葛,不过,人们若把表现这种恩怨与纠葛当成小说的目的本身,恐怕就失诸浅近,实际上,作者在这之上树起了一个更高的原则,并希由这个原则达致对历史的理性审判,此即“劳动神圣”;劳者有其食,不劳者与掠夺他人劳动者必遭报应,这思考贯穿了洼狸镇的历史风云,贯穿了老隋家的荣辱悲欢,也贯穿了所有的残酷、血腥和沉浮;在这幕巨大的戏剧里,表演者是禀性各异、积极而盲目的个体,而导演始终是那冥冥中永恒的正义,在它的面前,无论毁灭者或被毁灭者,实无胜利和失败可言,只有历史正义本身,是唯一的胜利者,隋抱朴苦苦参悟的,便是这样一种“绝对真理”,他手不释《共产党宣言》的细节,尽管理性色彩偏重,但于本书大义而言却如一道天光,因为结合小说的叙述来看,作者显然将马克思这部伟作从某种“政治经典”还原为人类正义原理,还原为劳动者的福音书,它宣示着最朴素也最终极的道理:劳动者不可侵犯,劳动者不可剥夺。很多人谈到《古船》与《柏慧》、《家族》手眼似非一人,我疑心他们是否真的读懂了《古船》。 不过,张炜对“劳动”和“劳动者”概念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理解,我想是反映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例如儒家中的“民”的概念,这概念基本以“农”为核心,“以民为本”跟“以农为本”大致同一——当然,这也与中国过去作为一农业社会的现实相符合。但我们看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的西方新教伦理,观点就有不同,对那些商人、金融家和企业业主,也渐认其为劳动者的一员,因这些人当中,确有一部分是靠辛勤劳作的清教徒精神创业致富的,其艰朴和敬业毫不输与耕种的农夫(虽然经营的手段因行业的特质好像多了一些心计或投机色彩),若读读汽车工业始祖之一的亨利﹒福特的传记即可略知一二;而且,从为社会创造财富上论,资本家们的贡献也不该抹煞,他们的产出、他们追求利润以及由这追求而带动的科技进步、创造的就业机会等等,都合乎历史之善,此外,他们中的诚实良善之辈在实现个人致富目的后将财富回报社会的行为,也反映了他们对“劳动”本质的正确认识(比尔﹒盖茨历年已捐出上百亿美元资助教育和平民,就说明一个劳动者远贪婪敬自“损”的共同素质)。当然,这类问题和现象比较复杂,常因民族、文化、宗教背景的制约而有千差万别的表现,比如,“金钱不总是罪恶的”这句话,在不同的现实里面它的对错可能就截然相反;张炜思想里敬农恶商的成分,实在也是有相当的现实根据,我只是在纯理论的意义上来指出这种思想并非完全合理而已。 但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传统价值观的偏见以外,张炜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理解,是超越阶级论和其他一般社会学观点而抵于抽象本质的,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劳动是人类的一种最高贵最纯正的品质,是一切优秀的无愧于其属性的“人”共有的特征。在其小说中,“劳动者”远远不仅是那些在田头或车间干体力活的人们,而是包括所有虔诚奉执自己的事业、孜孜以求、朴素、不投机、视劳作为快乐为立命之本的人们——比如,专注的艺术家、学者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张炜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比之于黧黑瘠苦的农民,不单没有什么不同,甚至,由于他们的劳动出于更自觉更内在的需求,而更体现出了劳动的真昧。中篇小说《请挽救艺术家》(1988)中的画家杨阳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的腼腆跟他对艺术的沉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心世界——由于在劳作中感到极度满足,而忘我而不知春秋。这个人物在1985年的中篇《童眸》里已出现过,显然他让作者感到难忘,所以三年后又专门以他为主人公写了另一篇。当然,更直接的例子,是像《冬天的阅读》之《耕作的诗人》这样的散文,“诗人”在此是指列﹒托尔斯泰。张炜这样写道:“对于他,稿纸和土地一样,笔和犁一样。于是他的稿纸就相当于一片田原,可以种植,可以催发鲜花、浇灌出果实。在这不息的劳作之中,他寻求着最大的真实,焕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激情。离开了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在诗人的最重要的几部文学著作之间的长长间隔里,我们都不难发现他怎样匍匐到土地上,与庄园里的农民,特别是是孩子和农妇们打成一片……”在对“劳动者”托尔斯泰其人做过一番描述后,张炜写出了位于他心灵最深处的一段话来:“一个人只有被淳朴的劳动完全遮盖、完全溶解的时候;只有在劳作的间隙,在喘息的时刻,仰望外部世界,那极大的陌生和惊讶阵阵袭来的时刻,才可能捕捉到什么,才有深深的感悟,才有非凡的发现。这种状态能够支持和滋养他饱满的诗情,给予他真正的创造力和判断力。舍此,便没有任何大激动,人的激动。”这些言语,有着浓厚的道德色彩,立场不同而欲从这一角度来质疑者自有其理;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这种表白,首先应引起我们对他的美学理想的思索,亦即,这种想法对写作意味着什么、构成什么影响? 很多年前,作者给《古船》隋式兄弟起的名字抱朴、见素,便曾于我有所触;尽管它们跟小说的内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我能断定的是,它们跟张炜的个人美学理想和文学追求却关系甚深。张炜文中,“质朴”“朴素”“淳朴”“简朴”一类词,出现频率之高是惊人的:“这种真正的质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重复”“一个作家只要真正展露自己的风格,只要朴素地写就行了。”“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挚、真诚和朴素。”“小说(指舍伍德﹒安德森的《手》)文字无比节省、简约,却表达了丰富的意蕴……”“好小说首先是简洁、朴素、自然。”“自然朴实是为文的第一要义。”…… 如果有一个词可以表达张炜经年于小说写作所保持不违的艺术面貌,那就是“质朴”。这个词大致上同时喻指了两层意思,一是精神上的,一是形式和语言上的。并且,它常常让我想到小说史上二位大师:托尔斯泰和海明威。这两个人,也是张炜最为心仪的对象,他一直用自己的作品对这两个大师表示着敬意;托尔斯泰从精神到小说叙事上的干净,不必说,始终是张炜心中力图接近的小说的最高境界,至于海明威,我认为张炜的短篇小说,特别是1988年以前诸多以渔村渔民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与之有着神似之处——不单单是语言运用的原则,也见诸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剪裁。此外,关于张炜小说的“质朴”特征,还有一个更高的事实,亦即,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没有尝试过使自己的艺术形式趋于表面繁复的变化,这是极其罕见的,不要忘记,这20年的中国小说是在一种何其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发展着,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作家置身其外,但是,张炜则接近于以不变应万变,除去他在90年代后对诗性的追求略有增加。 总的来说,对简约、质朴之美的爱好,是一种古风。在先秦,差不多各派作家都一致主张表达应该去奢就俭。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美学也建立在类似的精神上。此外,如果从文学和美学角度来看《圣经》,我们也发现,它的语言简质到了极点。这一切,可能起自古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现实,不过,文化的自动向抽象精神转移的功能以及历史积淀过程,却将它逐渐变成了一种美德、一种人文理想和一种艺术境界,变成了这样一种强大复杂的精神记忆。基本来说,艺术历来便是在简朴和繁奢两极间摇摆地发展着的。虽然后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已积累到远离抱朴见素的程度,艺术家对简朴境界的向往却从不稍减,反之,这种情结一现再现,甚至更显顽强。归根结底,在特定意义上说,艺术是一种反历史的以维护人的全部本质为己任的力量。从韩愈、托尔斯泰身上,我们便看到了艺术是怎样造就着这种人性。从对简朴之美的溯源来说,也可以认为,认同于这种美,便是自动地选择了向理想复归的精神位置,自动选择了现实否定的精神姿态,自动选择了复古的精神指向——所有尚朴的艺术家,无一例外。由此我们也看到,张炜在90年代突然被发现为“现代文明的反对者”实在是一个误会,但凡注意到他一贯的艺术旨趣,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意外”发现。当年,为六朝以来浮靡文风而疾首、力倡“古文”的韩愈,写过一篇《伯夷颂》,其中有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此文实为韩子个人的精神宣言,而以我看来,它也是可以一字不易地用在对张炜的创作和思想的解释上的。 如果本文流露出了什么“倾向”,我想也只是心性使然。但我希望阐明一点:实际上,我赞扬和渴望文学多种声音多种格局共存的局面——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多少作家,真正在寻找精神上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而不是像张岱之弟那样“转若飞篷”?这是真正令人不安、不屑以致厌恶的(当代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毁在了这种风气上)。反之,任何的“坚守”都值得尊重,哪怕它与我的个人信仰颇相牴牾乃至形若冰炭。 2000年7月29日 原载《钟山》2000年第6期 写作《古船》时,他是“藏起来的,先后换过一些地方”,先是在某军队招待所“找了一间小屋”,约半年后熟人来访渐多,作者再迁其所,“那是郊区山里的一座孤房子,真的长年不见阳光,是废弃不用的一个配电小屋,大若有十平方。”(《心事浩茫》,《张炜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动笔于1987年成稿于1992年的《九月寓言》,也出自类似的环境:“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藏在郊区的一个待迁的小房子里写出的,小房子有说不出的简陋。我朋友的这幢小房子隐蔽又安静,与吵声四起的街巷隔开了,不让我躁。这里也见不到通常的那些宣传品、刊物和报。外界的事情知道得不能再少了。”(《难忘的诗意和真实》,《张炜文集》第2卷。)作者的这种习惯,不仅是对写作环境的一种偏爱,其实同样反映着他对自己作品的内容、性质和情绪的看法——作为另一例子,我知道新生代的城市文学作家邱华栋,创作力最旺盛时的不少作品,是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间中写就。 《昨日里程》,见《瀛洲思絮录》,华夏出版社,1997。 上列诸文,收在《张炜文集》第6卷。 指明竟陵派的主要作者钟惺、谭元春。 明代末年江苏一有势力和影响的文人圈子;比较不喜欢个性主义的竟陵派,而赞许复古派的王世贞、李攀龙。 指王世贞、李攀龙。 这话题,实应大大展开,而引往对近世中国文学的根本困境的探讨上。我并不同意中国原有文化缺乏信仰层面的说法——这说法在中西文化比较上颇占上峰——我只认为,两者的不同是信仰体系的不同。但中国百余年来,旧有的信仰体系确实遭受极大破坏,外力内力的交逼已致其濒临崩势。恰恰是这原因(或者说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令近世中国文学的成就和力度,既愧于外国文学,也愧于自己的古代文学。一言以蔽,信仰内核的虚空化,是近世中国文学连续四代之衰(从整体而言)的罪魁。 其他几位,我认为是:路遥、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余华、李锐、张承志、刘庆邦。但提到他们,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于他们所有人的个人艺术和精神哲学。 《文学是生命的呼吸》,《张炜文集》第1卷。 我也想起李锐的“拒绝合唱”之说。80年代后期以来,文坛日益被各种时髦充斥,虽然这些时髦往往以怪异、奇特甚至高深的面目出现,但也无改它们作为“流行色”的通俗本质——就像留披肩发戴耳环的男人足够怪异,却其俗在骨一样。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彼此效仿之中获得意义的。 当有人问人性是不是“恶”的时,他这样说:“我认为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来概括。正因为是复杂的,所以可以分解和滋生出很多东西,可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善和恶等若干倾向。”(《期待回答的声音》,《张炜文集》,卷1) 《张炜文集》第6卷。 同上。 《你是艺术家,只要你不沉睡》,《张炜文集》第1卷。 见注11。 《珍品荐:手》,《张炜文集》第6卷。 《苛刻二题》,《张炜文集》第6卷。
九月寓言 作者简介
张 炜 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出版有《张炜文集》48卷。 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等多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等20部。 《古船》等入选新文学大系,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文小说之首等多个奖项。 《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获全国“五个一”奖、中国好书奖、畅销书奖等20余顶。
- >
推拿
推拿
¥12.2¥32.0 - >
伯纳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伯纳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15.9¥49.8 - >
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
¥17.2¥42.0 - >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一天的工作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一天的工作
¥16.0¥45.8 - >
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
¥26.9¥48.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6.7¥68.0 - >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40.6¥58.0 - >
莉莉和章鱼
莉莉和章鱼
¥16.0¥42.0
-
到山中去
¥17.7¥30 -
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12.8¥25 -
茶,汤和好天气
¥13.9¥28 -
极品美学
¥18.6¥58 -
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
¥15.3¥30 -
心安是归处:琦君创作60周年美文精选
¥15.9¥49.8